
私德和公德问题——
人是语言动物,每个人都有用语言表达自己、记录事物的自由和权利,你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是问题,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自由和责任之间永远存在着微妙的张力与平衡。如果你书写的文字局限于自娱自乐,在自媒体上分享给少数亲朋,这无可厚非,这时你写下的文字(诗歌)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织物,就和农妇自己编织自己穿的毛衣一样,随便你好看不好看,随便你什么款式花色。但是,一旦这语言的织物在公开正式的媒体上发表,它便从物品变成了产品,它就标了价,成了面向公众的文化产物的一部分,这时,它就从农妇自用的毛衣变成了一件他者需要花钱购买的商品。物品和商品,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前者属于私人之物,后者属于社会。既然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就必须接受读者的阅读检验,就和商品必须接受顾客的挑选和评价一个道理。
因此,读者对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诗歌进行评价,是完全正当的权利。就比如贾浅浅对屎尿秽物的喜爱,她在自己家里怎么喜欢都不为过,和别人无关,只要别熏到邻居,人毕竟是活在人类当中,而非真空里。所以,污秽之物是不适合在公共空间里拿来把玩欣赏的,进入公共空间的东西接受这个空间的规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不嫌屎尿熏人,别人可能并没有你那么大的承受力和海纳百川美丑无差别的超越境界,读者大多数还是凡人,不像诗人是无冕之王。可是这么一个常识,诗人居然不明白,也不承认,不遵守,他(她)硬是要把一坨坨金黄的屎块塞到别人鼻子底下,人家熏得赶紧躲开,并发出受冒犯的不满的声音,诗人不但不觉得自己挑衅侮辱了读者,反而认为读者不应该哼哼唧唧地抱怨,她甚至很是不解,这么香的大粪,读者怎么不感激她的分享,反而要表现出不满和遭受冒犯的愤怒呢?!
她甚至还联想起波德莱尔的《狗和香水瓶》:
“我美丽的小狗,我的好小狗,我可爱的杜杜,快过来!来闻一闻这极好的香水,这从城里最好的香水店里买来的!”
狗来了。这可怜的动物摇着尾巴,大概是和人一样表示微笑吧!它好奇地把湿滑的鼻子放在打开盖的香水瓶口上。它惊恐地向后一跳,并冲着我尖叫着,发出一种责备的声音。
“啊!该死的狗!如果我拿给你一包粪便,你会狂喜地去闻它,可能还会把它吞掉。你呀!我的忧郁人生的可鄙的伙伴,你多么像大多数读者;对他们,从来不能拿出最美的香水,因为这会激怒他们,而应该拿出精心选择的垃圾。”
诗人恰恰弄反了,读者不是像她一样喜爱秽物的狗,而是有头脑和心灵的人。诗人悻悻然,颇有知音难遇的落寞和委屈。嗯,这位诗人的嗅觉恐怕出了问题。她显然分不清粪便和香水。
按照常理,如果有陌生人在公共场合把屎往你脸上糊,你的自然反应是什么,那是可想而知的,你或者把她当成精神病,赶紧躲开,或者把那屎反过来啪一声糊她脸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可这个简单道理,在那些巧舌如簧的批评家们来看,是不成立的,他们认为,你要是自卫性地还击,那就是干涉诗人自由,是粗暴,是批判而不是批评,是不懂诗。
是非黑白就这样颠倒了乾坤,也颠倒了无辜的普罗大众,让大众乖乖跪倒在金灿灿的屎坨面前,为自己的无知,为自己不懂诗(屎)而后悔不迭甚至忏悔,然后乖乖滚出公共空间,留下一小撮诗人和诗人的吹鼓手们互相捏着屎块,如同王者归来,互相喂饲。
道德判断问题——
有人说,“道德可不可以审判?当然不行。因为没有人的道德是完美的。”这不是胡说八道的滚蛋逻辑吗?打个比方,你觉得厨师做菜不好吃,你想说不好吃,可因为你不是厨师,你就无权说厨师做菜不好吃。常识都不讲。读者和诗人批评其“你诗不好”,他们就说“你不懂”。还要祭出法宝,什么“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什么诗歌圈子内部的事,读者没资格评头品足。那么请问,所谓诗歌圈子内部都包含哪些人?谁是不是诗人,谁来定?诗之优劣,谁来判断?这些人,完全是睁眼说瞎话,他们不是不懂诗之优劣,而是坏。
社会层面的道德有相对性,它和集群文化、习惯和利害有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总是置身于某个结构之中,所以人都是“经济的人”。纯粹道德或全人类有共识的道德,恐怕还是平等自由博爱这些启蒙理想。文学的道德,和道德的文学,是两回事。文学离不开价值观世界观,缺失了道德与良知的文学,完全可以当做文字游戏。连强调文学自律的新批评派,也都知道,自律和他律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艾略特有言,文学之伟大绝不能仅仅从文学本身去判断。存在超道德的文学吗?形式本身就含有价值选择,趣味里边也包含价值选择,绝非趣味无争辩那么简单。喜欢屎尿的绝不会比喜欢黄金的心灵高贵。

要说对臧棣之流言论的驳斥,鲁太光的文章论说充分,学理严谨,破解了相关疑难。姑摘录几段:
庄子确确实实说过道在屎尿中,可援引这句话的人,好像忘了这话的语境。庄子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东郭子去问他道在哪里,庄子说“无所不在”。东郭子一定要他说个出处,他就说在“蝼蚁”,东郭子嫌庄子的回答太卑下,他就说在“稊稗”,东郭子嫌他越说越不靠谱,继续追问,问来问去,他就说在“屎溺”,彻底把东郭子的嘴给堵住了。可见,庄子并不认为道只在屎尿中,而是在宇宙万物中。再往下读读,我们还会知道,庄子是因为东郭子太愚钝,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对,才剑走偏锋,以屎尿为例刺激、启发他的。知道这个背景,就会发现,道“在屎溺”这句话对于贾浅浅“屎尿体”合理性的论证意义就极其有限了。当然,有人肯定会反驳说贾浅浅也没有光写“屎尿体”呀。这我当然知道,贾浅浅的诗,我还是认真看过一些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放大一些语境来理解,这个反驳就会彻底站不住脚。庄子是什么样的人呀?是一个神一样的人,是勘破世间万物的人,是一个齐物论者,是一个视名利如同屎尿的人。这样一个人,即使真写了“屎尿体”——看他的文章,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其洒脱逍遥,千古一人,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写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我们就是假设一下,说明道理罢了——恐怕也不会到处发表、出版,请人写评论,召开研讨会,说自己写的不是“屎尿体”,而是“黄金体”“珠玉体”,而后再用这样的“屎尿体”为自己换取物质利益或名声——在庄子眼中,这才是真屎尿!说一千道一万,贾浅浅的诗歌趣味跟庄子根本就不是一个路数,甚至截然相反,前者功利,后者虚静,用庄子来给贾浅浅站台,请错神了。
至于波德莱尔,那更是找错了对象。他们以为波德莱尔写过《恶之花》,写过腐尸,写过妓女,写过醉鬼,写过流浪汉,他自己也放浪形骸,特立独行,就一定能印证贾浅浅“屎尿体”的合理性。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他们光知道波德莱尔写过《恶之花》,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写《恶之花》。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波德莱尔不仅是名诗人,而且还是大评论家,他有不少关于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能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诗歌。许多人其实只知道波德莱尔写了《恶之花》,其实并没有认真读过他几首诗,于是才会见名忘实,误以为波德莱尔沉迷于“恶”,又把“恶”跟“脏”等同起来,以为他写的是“脏诗”,即“屎尿体”。其实,波德莱尔之所以写“恶”,是为了发掘“美”,他曾说过,自己最高贵的事业是化腐朽为神奇,是“你给我污泥,我把它变成黄金”。他还说过:“丑恶经过艺术的表现而化为美,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这是艺术最奇妙的特权之一。”其实,只要看到这几句话,理解其意思,我们就会知道贾浅浅的诗歌趣味离波德莱尔有多么遥远。
客观地说,还是有一些说得过去的诗。但这些诗,不过是一个现代社会“小 确幸”的自我展示——她展示自己的爱情、友情、亲情,甚至展示自己的性爱及其欢愉。说句实在话,由于大多数诗作分寸掌握得还可以,因而并不让人反感,有的还有些小清新。但我们必须指出,支撑这种诗歌的内在情感是一种现代市民的自我满足感。在现实中,这种自我满足感值得尊重也应该尊重,但这种自我们满足感如何获得诗意,即如何“诗化”,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就美学而言,这种自我满足的底色是平庸,而平庸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庸俗,甚至低俗。我们可以说,“浅浅体”尚可理解,因为它最大的问题不过是平庸,而“屎尿体”则不可理解,因为它庸俗。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明白,波德莱尔诗歌“反叛”的正是一切像贾浅浅这样的诗作中平庸的小市民美学。所以,那些以波德莱尔的诗作为由头为贾浅浅站台的人,与其说是为她辩护,不如说是打她脸。
鲁太光 | 评论家先生:前方“围城”!——也谈“浅浅体”“屎尿体”诗歌事件

贾浅浅还有一首名诗,《希望》,亵渎了人类的爱情,作者分不清爱和性的关系,她在看到别人的幸福时,心里恶狠狠地想着,那不过是“女人裙子下两腿间流出来的东西,和男人内裤的气味,深深地混淆在一起。”而在她写自己的性时,却充满了圣洁灵魂的无限度升华。我就纳闷,一个人怎么能在面对别人的爱情甜蜜时产生那么恶心的念头,而涉及到自己的“爱情”时却写得那么圣洁让人不可理解。按理,一个人对同一件事物的判断不应该这么“双轨”,按照她自己的逻辑,也应该是恶心的流体和内裤的气味啊。
真真受不了,打住打住。
还有个好玩的,有图有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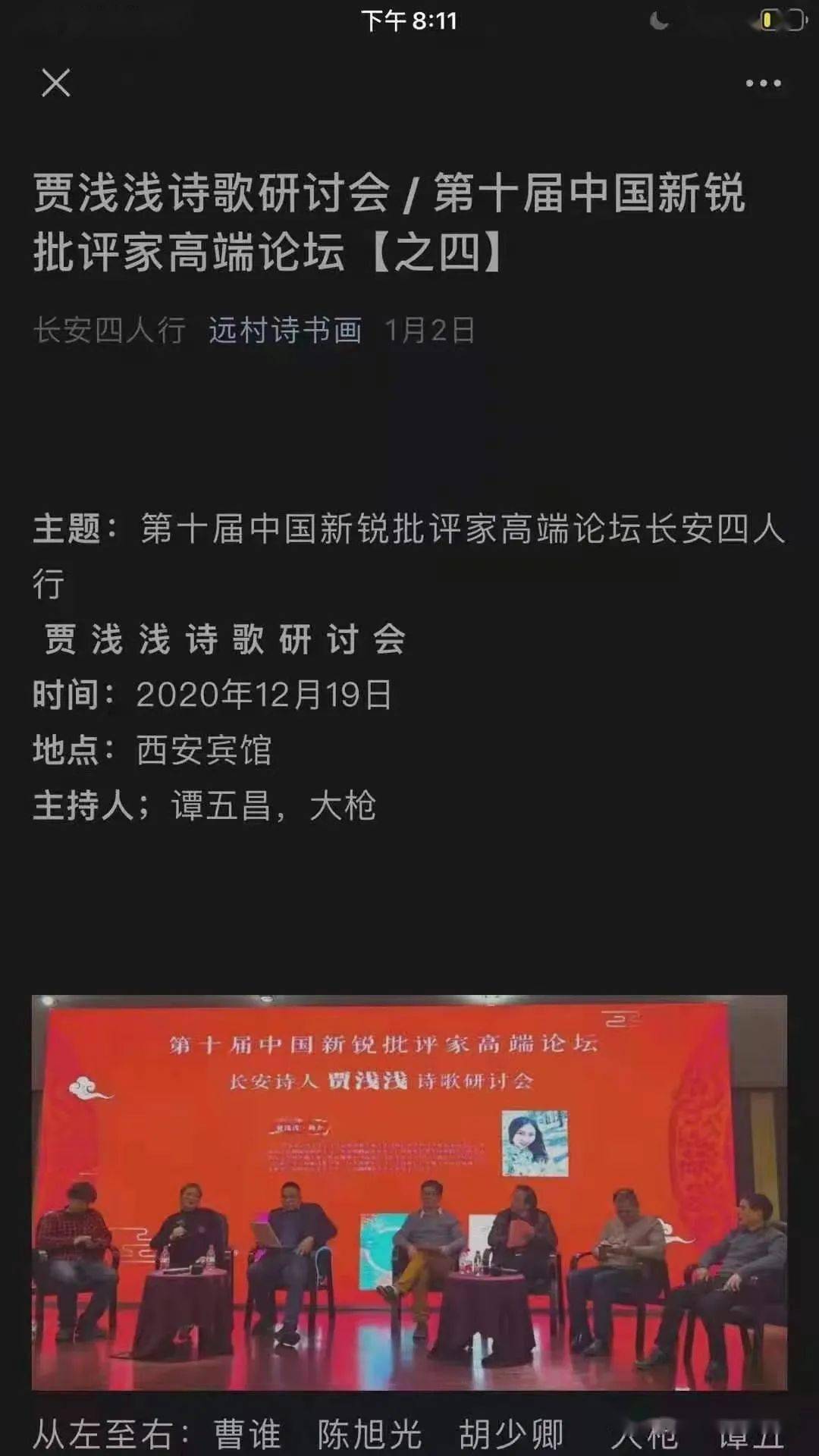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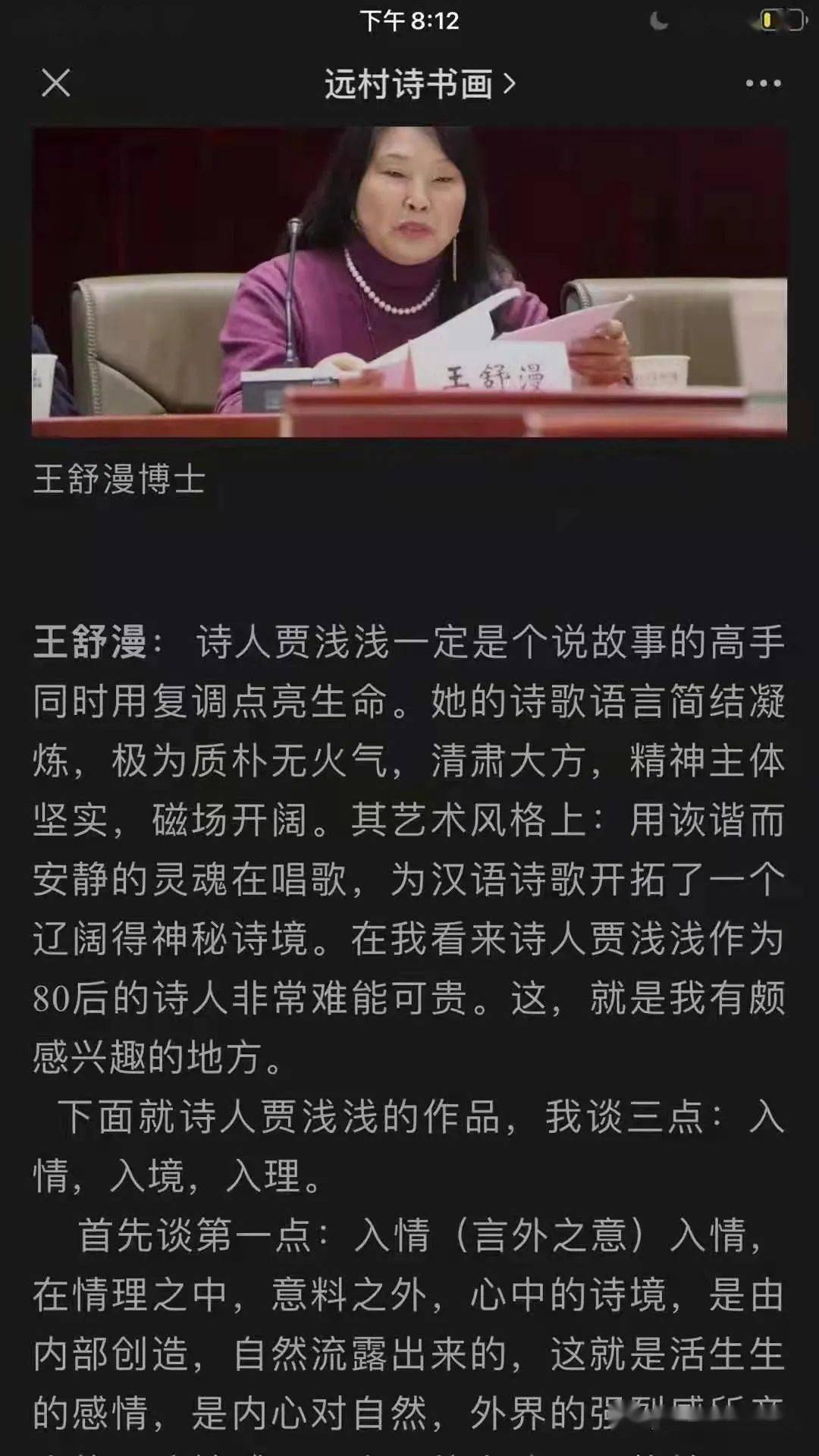
这明明是复制1999年台湾唐山版“大陆先锋诗丛”中我那本《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的序言啊,哈哈,此女博士资料爬梳、将原文分散和碎片化再予以拼贴的后现代功夫可真是不俗呢。为了吹捧贾浅浅,至于这样高射炮打蚊子吗?
从遥远的东北传来一击黑暗、冷冽、坦荡的钟声,回响十方。马永波的诗质迥异于齐鲁、荆楚、巴蜀、吴越、台闽诸地域文化,风格独绝另出一系。在他的诗里你可以感受到探求存有实相永不歇止的饥饿感,不存一丝侥幸,不企求救赎,没有可变空隙的严苛生存造就了马永波正向存有的勇气与决心。层层揭示、内外思量,以多重视镜的 复调写作深入黑暗与寂静,照亮死亡与生命,尚有无可比肩的彻骨之寒。他的诗 清肃、大方,精神主体坚实,磁场开阔,富有北方寒地清冽的气息, 为汉语诗歌开拓了一个辽阔得无法估量的神秘诗境。(黄粱,台湾诗人,评论家,编辑,艺术策展人)

算了算了。
要根治这种病态,“难度写作”可以作为一剂良药,参见本公众号《贾浅浅事件观察(3)| 重新倡导不合时宜的难度写作》,但我想,贾浅浅们绝不会听我的,绝不会变得深深,难度,那多累啊,还是回车键简单。
点击链接: 贾浅浅事件观察(3)
再附录一个较新的思考,《重新回归“记录诗学”》
马永波
1994年我曾明确提出,诗在现时代最重要的任务和责任是触及真实,它涉及到“记录”这样一种写作策略,认为“呈本真状态的事物都是诗”,我们只需记录下来即可。当时的想法自然和现象学的还原有关,与解构主义的去弊有关,思考的是如何透过权力和语言的虚构而照见真实,这真实自然包括物的真实,事的真实,更是心的真实,因为,在这一切之后,起统摄作用的,是神的真实,是依照祂口授于我们心中的方式记录而成,这种记录不是照相写实主义,也不是后现代的抄写大脑,而是超越了主客对立的互摄。
90年代的所谓个人化写作,对于消解宏大叙事当然有其贡献,它使得写作真正回到个体自我(而非代言人式的集体性自我)日常的所思所感,将写作的本然还给了自身应在的位置,这是对朦胧诗写作范式的重大反拨和纠偏,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危险的趋势,诗写者(用这个词语来指称是因为大多数诗歌工作者只是分行者而不是诗人)往往流于一己的满地鸡毛,个人情致,小情小绪,丧失了对人类普遍处境的关怀和道德担当,沉迷于琐碎之物的把玩和迷恋,同时,八十年代生机勃发的探索精神似乎也失去了动力,普遍陷于庸常,语言形式和更重要的诗歌精神两方面都没有大的进展。
到了新世纪网络时代,先锋诗歌进一步后卫化,成名者故步自封,能原地踏步而不被地球旋转甩在后头,已经是不错的了,鲜有在精神和技艺持续掘进的勇者。或是继续修辞性玄学性(实际是一知半解的玩玄)静态书写,和时代脱节和平行;或是以庸俗的小市民意识形态为乐,在泥坑里打滚,泼溅黑了吧唧的浪花;或是在根本没有对古典诗学的前提和存在的自然与社会文化条件进行谨慎反思的情况下,便消化不良地化用(误用)明清时代笔记小品的语汇,来将自己并不典雅的自我装修得飞檐走壁,做出一幅看透世事风轻云淡的高境界姿态,实则令人作呕;或是对诗进行对象化的有距离的书写,没有个人生命体验的渗透和彻骨之痛,看似高杨批判现实、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只是词语层面的姿态,只是用道德来攻击别人而同时将自己置于不容置疑的道德优势之上,甚至以表面的反抗来暗中献媚,这种写作之于前述种种表面形态不同但内里均为玩弄辞藻之闺戏的诗,更有危害,基本可以判定为伪君子之行径,比之真小人还具有欺骗性。
在此,根本无需再继续进行类型学的梳理,只要还有起码的审美判断力,放眼望去,当代汉语诗歌,一片荒芜又狂欢的景象。大音希声,黄钟毁弃。个体心灵的大面积荒芜而不自知,自我的普遍异化腐化和主动犬儒化,对现实苦难的视而不见,甚至以小布尔乔亚的廉价温情来涂抹和遮挡苦难之实存,对人类共同体何去何从的命运漠然无知,对无处不在渗透到毛细血管的恐惧和谎言知而不言……凡此种种皆为诗的耻辱,外在的苦难和内在的真实在能指滑动的书写中均告遗忘和消失,代之以歌舞升平的颂歌,和不疼不痒的自我抚摸。
在这种形势下,我呼吁真正有骨气有勇气的诗人,回到诗歌最基本的功能上来,那就是杜甫的以诗为史的传统,将这个时代的真相记录下来,留给后世。不要再以你那自得其乐的哼哼唧唧,毫无意义的词语游戏,故作高深的虚伪粉饰,看似慷慨热血的反向趋附,不要再以苍蝇般的众声喧哗,再度将早就被割断了喉咙的可怜缪斯那微弱的痛楚难当的颤抖之音,彻底淹没在这嗡嗡嗡嗡机器般的打着诗歌旗号的赞美与感恩的齐唱声中。午夜梦回,要扪心自问,你到底写了些什么,你到底感受和思考了些什么,我相信,即便是苍蝇,也还是有一颗小小的心脏的。如果经过彻底的反思,你还是觉得自己的诗果真有价值,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已经提前进入了死者的行列,而且绝不会在最后审判中站立得住,绝不会有机会身体复活,你的永恒将是永远的公义之刑罚,正如但丁所言,在重大道德危机的时刻,只顾自己的人,地狱中火焰最为炽烈的地方就是为其准备的。
记录,这就是目前诗歌的首要方针,记录下一切,即便置身事实之中,我们作为有限个体因无法具有上帝全知视角而难明究竟,但依然要凭借你在具体事物上的谨慎把捉、凭借你的良知和理性逻辑、凭借你的创造性直觉,将一切记录下来。这记录可以不美,可以没有传统的诗意,但其忠实于人性、常识和道德底线,忠实于天国理想的唯一盼望,而终将会在后世成为一份时代的证据,让后人能够从中破译出我们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价值远远大于所谓的艺术之诗,所谓的超脱利害的美学之诗,所谓的怡情悦性和调剂生活……
微博时代我曾言及,当代汉诗的阅读经验仍然是令人不快的,既缺乏精神的高度,也缺乏经验的宽度和思想的深度,属于“三无产品”,多是词语和词语做鬼脸,由此我倡导三度论为基础的难度写作,然应者寥寥,二十年过去,浅表性浮泛化无病呻吟的书写愈演愈烈,巨量词语生产对现实真相构成了又一轮遮蔽,心灵被窒息,苦难被遗忘,甚至积极认可没有苦难,没有异化,没有暴力,没有虚构……这样的“诗”是对诗的背叛,终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重回“记录诗学”!
让真理之光透过词语照亮这片我们生兹在兹的大地。
让心灵自觉不自觉的腐败赤裸裸地呈现。
让信仰者的牺牲为世人所明了而不是遭到嘲笑。
让世界的真实、自我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理大白于天下。
舍此无他,起码在现阶段,舍此无他,皆为堕落。
80年代,诗歌面对的外部压力来自意识形态,90年代经济强权又压上来,新世纪,庸俗乃至恶俗的小市民意识形态又成了一座大山,三座大山压在诗歌头顶上,诸君认为有出路吗?
可我依然不沮丧,诗乃祈祷,它会停留在空中。最后,以我的一首与缪斯共患难的诗做结。
我已经这样生活了五十五年我已不想改变
我已经这样生活了五十五年我已不想改变
我也没有力气改变了
为了不被你们的世界改变我已经几乎耗尽了能量
我只是个愤怒孤独的诗人,并且永远如此
面对社会之黑暗,民生之疾苦,个体心灵之困境
但凡还是个人,就绝不会什么心态平和风花雪月
更何况我是诗人,杜甫的左邻,陶潜的右舍
马雅可夫斯基的兄弟,聂鲁达的邮差
和惠特曼一起天天往前走的孩子
是埃利蒂斯布置在石榴树下的哨兵
和他一起面对篡位者的黑衬衫
和体制化暴力浆得笔挺的小白领
是波德莱尔的追云者,卡夫卡小写的k
是黑海边的奥维德,古拉格群岛上
被满身糊了石膏动弹不得的囚犯
你们的豪门后门和各种颜色的暗门
我都避之唯恐不及,它们只是通向地狱的翻盖陷阱
我不屑遵守你们的规则和潜规则
你们想把上帝安置在人心底的良知潜规则
那还真比叫西西弗斯坐在自己石头上还难
那必须得能抗得住我这战士后代的铁拳
和每条至少五十斤粗毛大腿的横扫
不信试试,我一条腿压你们那小细脖上
管保你那小豆芽脑袋抬都抬不起来
你们尽可以把鲁迅从教科书中偷偷删除
把鲁迅都得不上的鲁奖给潜规则成祥林嫂
但你们休想把马变成驴,尽管你们可以卸磨杀驴
也可以指鹿为马
就和当年那些英国小爬虫小鼻子小眼睛一个妈样
一见雪莱这巨人出现,就蜂拥而上
糊在脚背上猛劲叮咬
而这愤怒而孤独的巨人却打不中你们
因为你们数量太多,头太小
你们利用金钱和权势嫖了缪斯
玩弄了诗歌侮辱了诗人欺骗了纳税人
可是我那裙裾碎裂满面泪痕
但依然高大美丽的缪斯女神
她怀抱的家族神像依然完整光洁
哪怕她在奴隶那无尽的灰暗行列里
也高昂着倔强的尖下颏
灰色的明眸仰望着高天的光明
而我,就站在她的身后,锁骨上穿着铁链
这无尽的沉默坚忍的队列一直排过巨浪拍打之后空虚一片的海滩
一直排向普罗米修斯被缚的高加索悬崖
这队列缓慢地跟随最前端的缪斯女神
几乎像是静止不动地在沉思命运的奥秘
可终有一天,当最后审判的号角从云中吹响
这奴隶的队列会瞬间变为一支,解放的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