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看来,说真话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在当下中国,说真话居然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甚至是可怕的代价。在生活中人们在说真话方面还可以有一些伸缩余地,比如,善良的谎言。但是我一直坚持,在诗中不能有谎言,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我突然想到这句话,不能入诗的来入梦了。有些东西的确无法写进诗中,或是难以言表,或是写出来会招致非议,进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和危险。
叶嘉莹言,词之美感特质在乎 “弱德之美”,《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固然是一种弱德之美,即使是豪放派的苏、辛词之佳者,其所含的也同样是一种弱德之美。
而当代汉诗的弱德之美,和言说环境有关,诗人内心的真实无法真实说出,真实说出的代价是任何个体承受不住的,便只能以深致婉曲的隐喻象征暗示来隐晦地表达出来,需要以重重遮盖扭曲的修辞来“拒否”,让别人,尤其别有用心喜欢断章取义实施构陷的人无法看懂。
这一周多以来,持续关注贾浅浅事件,本来不想发言,直到看见新京报的臧棣访谈,其不讲学理人身谩骂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让人实在忍无可忍。作为北大教授,要知道自己的话举足轻重,会误导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我相信,这样的教授会带坏很多学生,让他们没有正确的道德立场。臧棣不是个没文化的人,他心里自然明白贾浅浅的诗不值一提,却又信口雌黄,原因在于其幽暗的心理状态,因为此前,唐小林有专文批判过他的诗。
我注意到,最初热捧贾浅浅的所谓批评家中,并没有臧棣,贾浅浅被广大网民和读者骂上热搜,风头一时无两,这时有媒体采访到臧棣,他当然会借机一泄私愤。所以,他不是不懂诗之优劣,而是故意为之,可见用心之复杂。为了私愤,居然放弃自己心中的诗歌标准和知识分子良知,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这一点,倒是一般人只能望其项背的。无独有偶,臧棣这些年还攻击过林贤治和北岛。
我素来简静,闭门索居,沉浸在书中,不关注诗坛的事,也基本不读现当代汉语诗歌,觉得没啥意思,与自己通过外语接触到的诗相比,云泥之别。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激发不起我的阅读欲望。
这次贾浅浅事件我站出来发言,且文辞犀利,直指为其张目的某些诗评家,不但在公号公开以文章予以驳斥,也在微信私聊里直接质疑他们,恐怕只会带给我更多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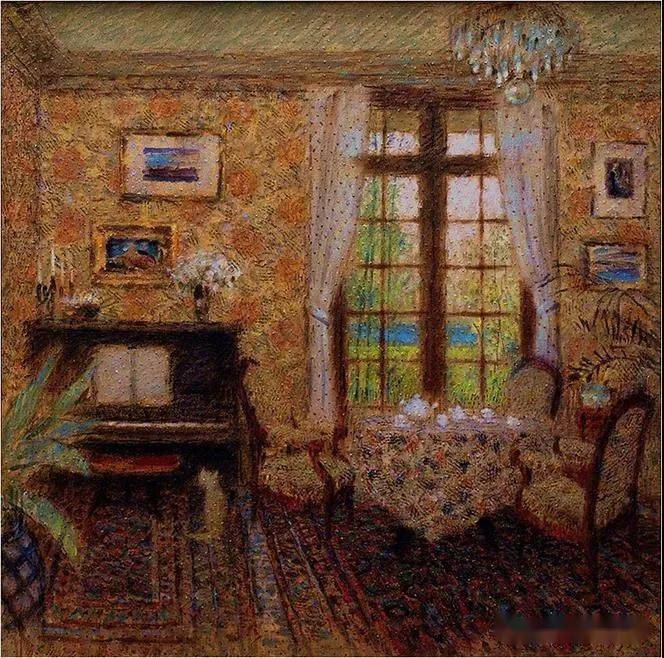
说起来,我与张清华认识也有二十年了,在济南北京南京都有数面之缘,世纪初我和元正爬泰山,曾去济南会诗友,清华请我们吃鲍鱼,结果,我和元正这两个草根傻缺,不认识鲍鱼,我悄声问元正这是啥,元正说是一种贝类,这时,委屈的清华轻声说,鲍鱼鲍鱼。后来我才知道,鲍鱼很贵,给我们吃真是白瞎了。那时的清华,还是很正直有人味的。他去北京工作后,我也曾去看过他,本来他都食堂打好了饭菜,我因为路不熟,到得晚了,菜凉了,他便重新带我去饭店,很有做朋友的意思。2007我刚到南京教书时,一早他微信我,要见见我,我说中午我请他尝尝淮扬菜,他说都是朋友不必客气,让我中午去他开会的地方和他一起吃会议饭,反正一个房间两张餐劵,他一个人住,不吃也是浪费。这时的清华,依然是个温暖的朋友。我喜欢把所有来到我生命中的人当朋友,这性格往往给我带来意外和伤害。也许清华从一开始就仅仅是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半生不熟的人。
再说说臧棣,这个我90年代前期就认识的人。一开始也还是很友善,他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时,还打算出我翻译的毕肖普,有一次我爱人大玲出差去北京,他俩还和特务接头一样约好在天安门的一个厕所附近碰头,给我捎书,这事让我笑了好久,其原因是我爱人不熟悉路,臧棣只好约在好找的厕所附近,哈哈,大玲回来和我说,感觉臧棣像个小孩一样,他身高和我仿佛,应该有186,却很单纯的一个书生。他编里尔克诗选,也曾收录我译的十四行诗的注解,那些注解非常难译。我是帮张曙光的忙。曙光曾跟我在我单位的培训班学过几天外语,我的老师是哈工大周之南教授,现在是语言学方向博导,曾帮我校过河北教育版的阿什贝利。
90年代的臧棣应该还是比较纯粹的书生。他性格的变化或者说道德上的滑坡,应该是在1999年参与知识分子与民间帮之争以后。也许从那时起,他恍然大悟,原来诗歌江湖并非那么干净,那么有原则。盘峰论剑后,我与这两方都彻底疏远了,这是我的主动选择,本来两个阵营里都有我的朋友,我颇为赞同沈奇大哥的说法,80年代诗人之间还是观念之争,到了90年代却成了利益之争。所以我认为两方都已堕落,干脆敬而远之吧。
新世纪后,我和臧棣很少有交集,大概2010年左右,我陪我的博士后导师孙绍振教授在杭州开会,洪子诚师叔也在,谈起他来,我和臧棣通过一个短信,他言及让我给他台湾唐山版诗集写个书评,我当时正在写出站报告,便说书评不写,但会在出站报告里写到。我不是敏捷的作家,尤其写评论文章,往往要焦虑一个月乃至还要失眠,才能写出三四千字。
台湾这套大陆先锋诗丛,影响很大,它是黄粱一人之力,公开征稿而成。第一辑是1999年出版的,我投稿投中,那辑收录九个人的个人诗集,还有一本九人文论合集。海上、余怒、马永波、孟浪、柏桦、于坚、虹影、周伦佑、朱文。十年后,2009年,出了第二辑,臧棣、车前子、伊沙等收录其中。臧棣出道很晚,90年代初我们在西渡家里认识时,我还根本没听说过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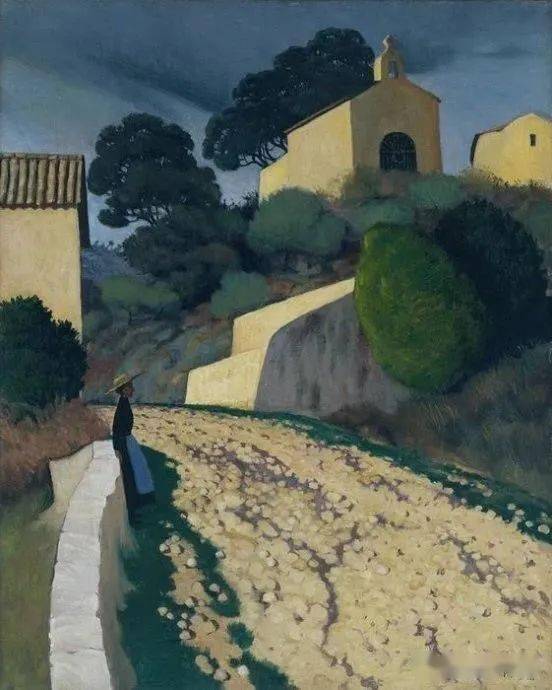
关于他性情甚或人格的变化乃至变异,其实有迹可循。2013年我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就曾引来他的人身攻击的谩骂。我的言论如下 :
“汉诗的阅读经验越来越让人不快,既缺乏精神的高度,又缺乏经验的宽度和体验的深度,三无产品,有的只是词语和词语互相做鬼脸。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写作诗歌30年的诗人,我深感悲哀和愤怒。”
臧棣怎么骂人的,我微博没删,大家可以去查证,围观,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同是博士教授,为人为文区别甚大,不可同日而语。
真是好生奇怪,只要你批评汉诗,有些自以为代表了诗的人就跳出来。此次贾浅浅事件,臧棣依然故我,人格修养学术水平毫无进步,“傻逼”挂在嘴上,同行与之探讨学术,他不正面回应,就是爆粗拉黑。读者质疑时,他反倒满口学术振振有词。这策略颇能混淆视听,纯粹是臭无赖。
又有资料显示,他也曾攻击过林贤治和北岛,且长篇大论数万言。
2006年下半年,林贤治以《西湖》为阵地,集束式推出包括《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向何处去》《非政治化:媚雅与媚俗》在内的系列批评文章,对“第三代”及其后的诗歌做出“非政治化,非社会化”的否定性评判。其中, 对以臧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尤为严厉,斥责其一味追求知识性、抽象性和学院化,以知识阻断诗歌与社会的交往,用技艺消解诗歌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麻木、自闭、缺乏痛感,是一种处于阉割状态的奴性写作。
2007年受邀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后,北岛多次批评当下大陆诗坛,相关文章可见2009年第二届“中坤诗歌奖”的受奖辞《缺席与在场》、同年写就的短文《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2049年的读者》,以及2011年7月在香港书展所作的演讲《古老的敌意》等。北岛的总体观点是, 在商业化与体制化的合力围剿下,诗歌放弃了对现实和历史的关注,丧失了苦难意识和精神向度,词与物脱节,沉溺于无意义的语言狂欢。汉语诗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此,北岛特意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里借来了“古老的敌意”这一锦囊,指出优秀的诗人第一要与时代保持敌意,对主流话语保持警惕,第二要与母语保持敌意,挣脱行话与娱乐语言的束缚,恢复汉语的命名功能,第三要对诗人自己保持敌意,牢牢捍卫自己的精神防线。
对于臧棣的攻击,林贤治和北岛都没有回应。这是他们的姿态,代际不同,理念和性情也不同。林老师是我素来敬重的作家和批评家。多年前他曾寄给过我他编的书,邀请我翻译些东欧作家的思想随笔,资料所限,我没能参与。后来,林老师又请我翻译惠特曼散文,2015年我去广州给我的诗集做签名本,在编辑王凯和诗人远人陪同下与林老师见了一面,据他说,他考察了所有惠特曼译者,最终决定启用我,何其信任有加,这对我有很大鼓舞。惠特曼词汇量太大,散文芜杂丰富,涉及的东西太多,并不比他的诗好译。元正有回去我家,看到原文书立桌子上和砖头一样,小字密密麻麻,当场一口冷气,这哪里是人能做的事啊。我翻译时可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抠啊,标点符号都算上,它们也有相当的表意作用,也得安排得仔细妥帖。
不日前我曾和林老师通过电话,他说了些臧棣攻击他的事,他说臧棣后来见到他时,对他很是恭敬,林老师不由得感觉当初批判他的诗不是诗,有点歉意,这歉意当然是指人的层面,是一种人性化的东西,他本来就是对事不对人,涉及到诗,再好的朋友,也是该批就批。我非常赞同林老师的这种观念和做法。人是人,诗是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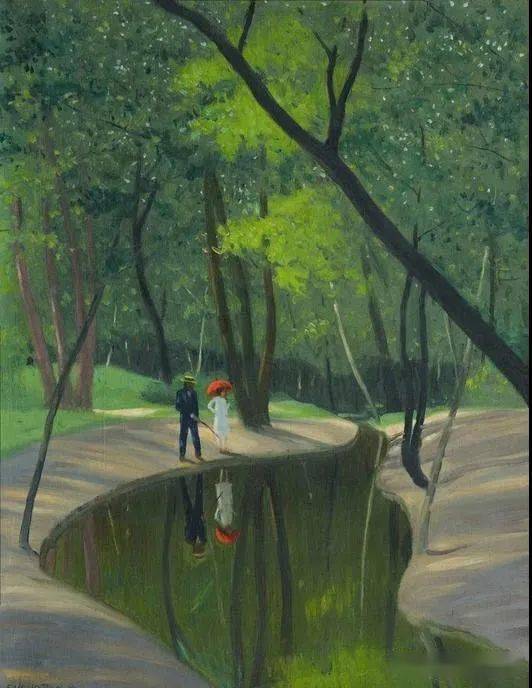
但这次臧棣给贾浅浅舔菊,实在有违诗人的良知,也明显表现出道德上的堕落。
有鉴于此,我的义愤勃然而生。连续在公众号发声痛斥之。事后,有不少朋友劝我何必如此,比如我的一位同门师兄说——
“在江湖上,都是出来混的,谁都不容易,最好不要树敌太多,因为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道理有道理的立场,自认为最有道理的,往往最没道理,比如不同政党之间的观点等。忙年代,我们应该学会逍遥自在,诗意时光。而面对诗坛如此情状,更应笑傲江湖,何必去趟这浑水,说真的,得不偿失。马上过年了,开心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