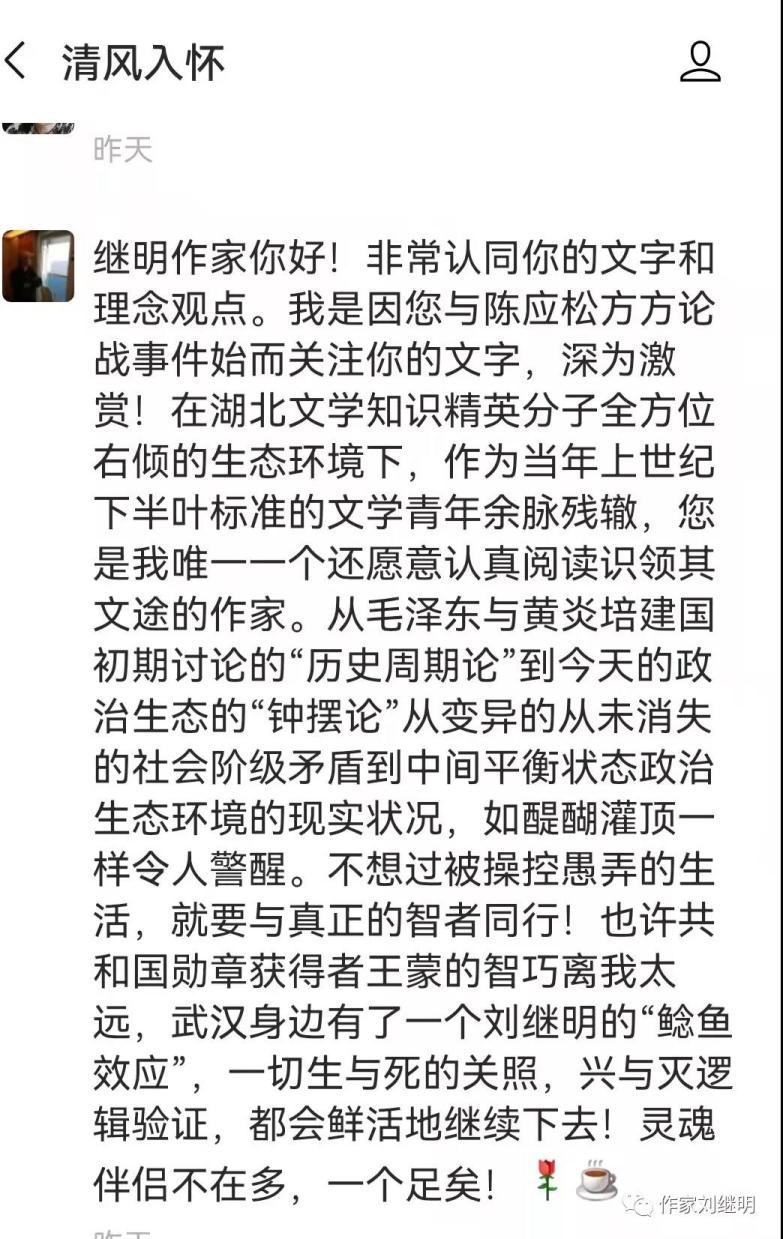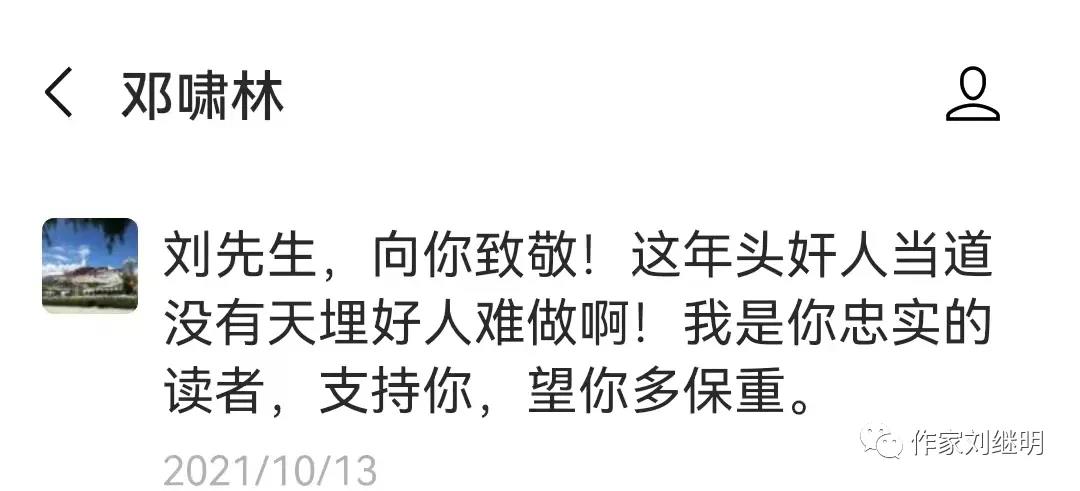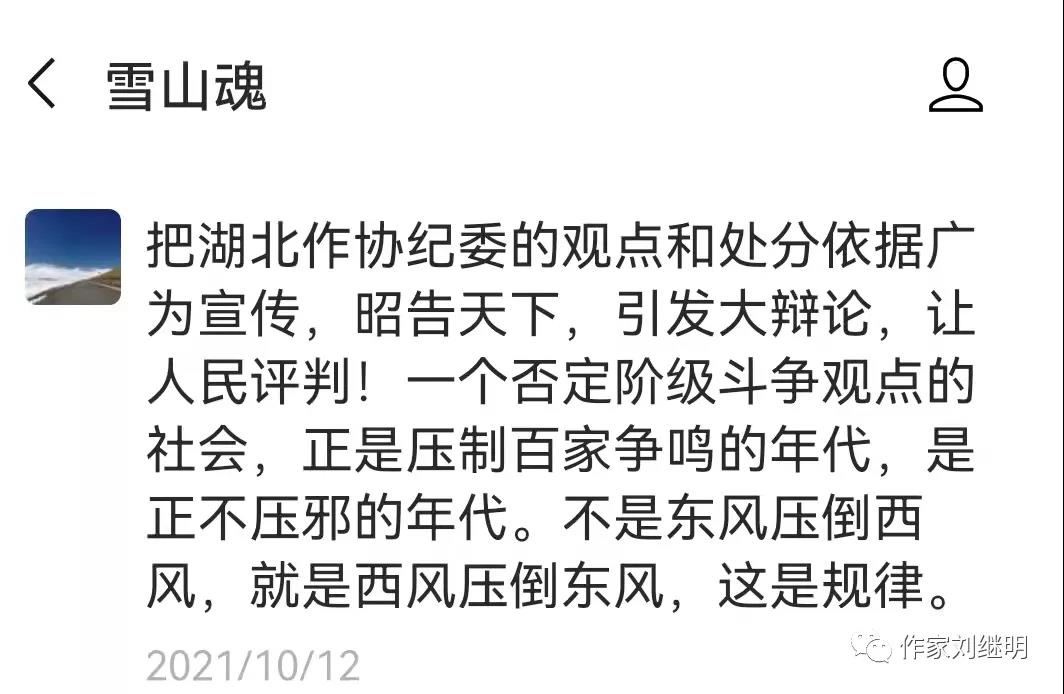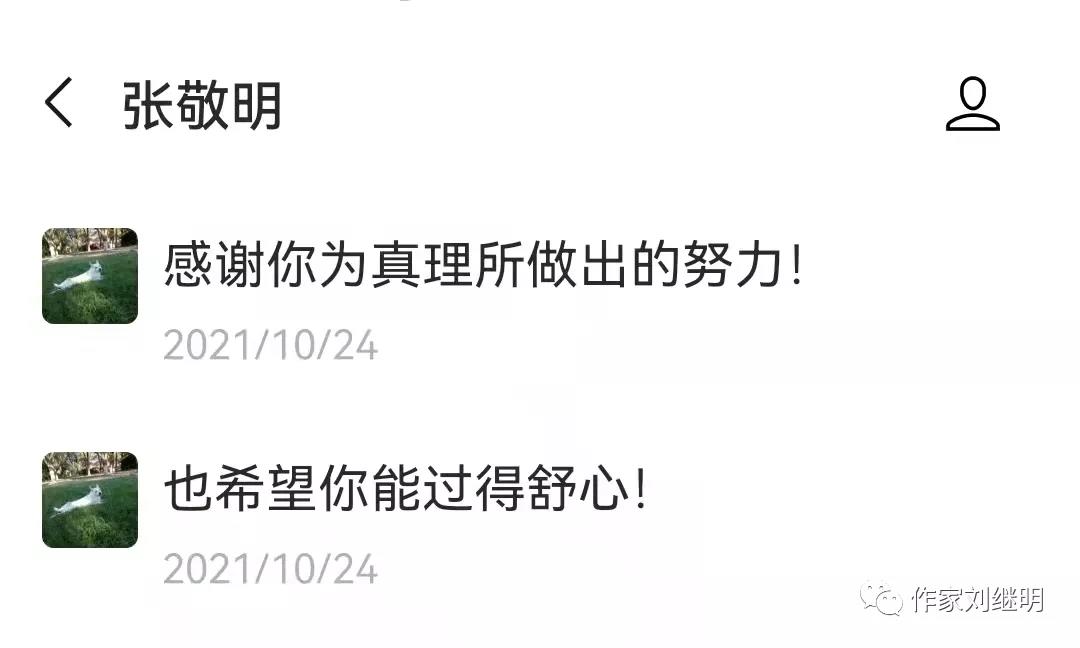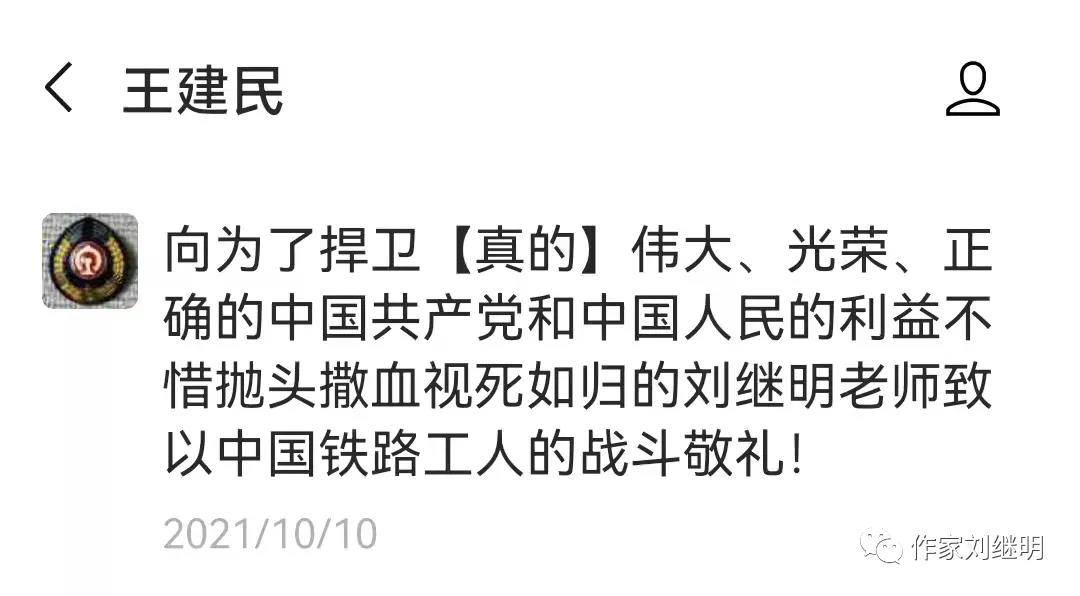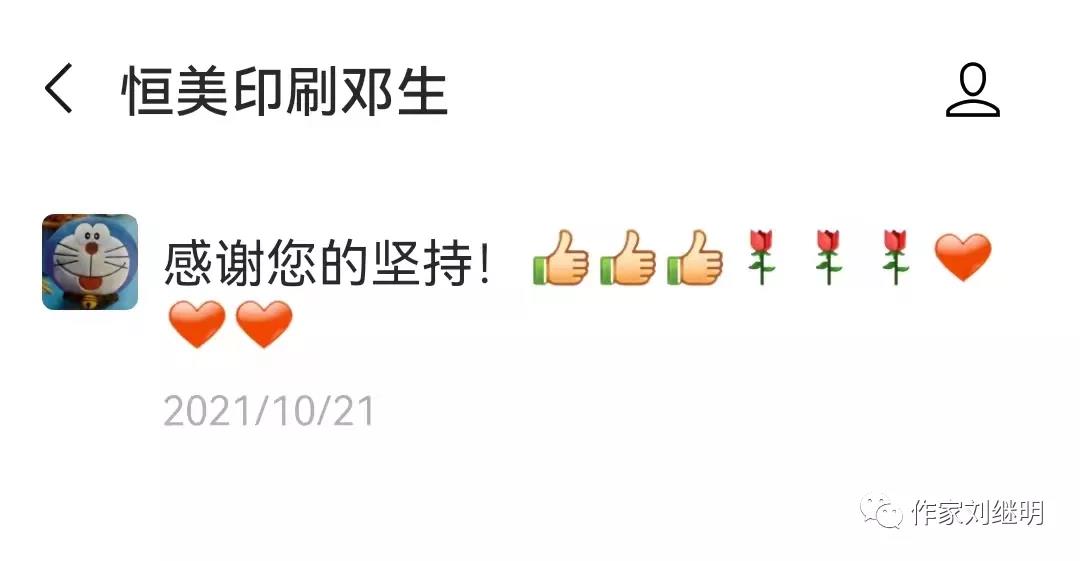阅读刘继明与沙黑合作的长篇小说《多余的人》后,有无限的感慨。主角郁平和他的妻子乔丽的一生,就像是一部教科书那样,深刻地具现了现代性与人自身命运的纠葛。
郁平从传统乡村进入现代,最初是因为参加革命队伍,后来是革命胜利后的工作单位中间,其命运由此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控,现在,是自己无法控制甚至是难于知情的权力之手,在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权力之手如何运作,也远谈不上公正。
《多余的人》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凸现了郁平一生的坎坷经历,基于个体亲历的经验厚度,实现了叙事的深度,对文革、现代性和主体命运的思考,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主角们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之间的徘徊往复
主角郁平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算是旧时代乡村的上层人士,因此,具有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他和他的哥哥都具有对于旧社会的自主批判性,由此,都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正是在共产党的干校中间,郁平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与同学和上级的行动互动和思想交流,在小说的画卷内展开。1945年日寇投降之后,1946年6月国民党开始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彼时弱势的共产党军队选择了“北撤”,郁平因病未能随队,由此留在后方。正是在这里,展开小说的矛盾,其同乡庄世庭先是带来锄奸队镇压了郁平的哥哥,随后,庄世庭自己因为无故离队被作为锄奸对象,阴差阳错之下,郁平还在锄奸队要求下,在追捕庄世庭的路上开了一枪。
很显然,旧社会对于其统治阶级成员而言,都已经丧失了说服力,因是之故,相当大一批上层阶级的子弟,也为马克思这样的名字和革命思想所吸引,离开家庭,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在乡村那个熟人社会中间,郁家与庄家作为地方上的统治性存在,彼此间存在着长期的利益关系竞争,也存在着各种人际情感纠葛,庄世庭的堂姐还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在革命队伍内部,两家的青年一代又重逢,还无意之间延续了从前的竞争模式。旧时代的竞争关系和矛盾,被无形之中带进去革命队伍内部和新社会中间。
在革命后时代,郁平先是在省报编辑位置上工作,后来又选择退出权力场域,选择了教师职业,当然,他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资历的高级别教师。身具这样的光环,事业与人生的起点都不错,在这个背景下他邂逅了自己的妻子乔丽,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并育有一子。好时光结束于1959年的内部审干,郁平被怀疑有叛卖嫌疑,开除公职且遣返农村故乡。
妻子乔丽一个人带着小孩在城,然后还失去了曾经的好房子,搬去陋巷居住,在身心俱疲和前途恐惧之下,乔丽精神出了问题,她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次次深夜徘徊,某次夜间竟然无意识之间堕入河中,还淹死了自己的儿子,为此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郁平遭此厄运,丧失了事业和家庭的一切,他为此多次申诉,但始终得不到解决。事后得知,郁平的冤屈与同乡庄世庭有关,他恰好是主管审干工作的副市长,郁平的案子以莫须有的证据定案,就是在他的主管之下。
数年迁延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郁平又一次被选择作为批判对象“抛出来”供群众批判,甚至,还在批判大会上被逮捕入狱。
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人民革命,文革中出现的群众性组织及其批判性锋芒,与行政体系独立掌握权力监察民众不同,是群众组织起来对行政体系展开批判性审查和发声。正是在这样的反常时期,在群众的批判性压力之下,郁平被从监狱内放出来了。
郁平遭遇冤屈,最后家破人亡,多年在组织渠道内部多次上访均得不到解决,现在,郁平有了新的表达机会和空间,然后,毫无疑问,郁平是在学生的动员之下,写出了他的大字报,对官场的“公器私用”此种机会主义展开了一次有力的批判。就这样,郁平带着相当程度的自觉,参与了群众对官场的有组织批判活动,具有了“造反派经历”,结果,他因此在1977年再一次被捕入狱。
在暗中操控郁平命运的“权力之手”,就是庄世庭,文革期间,罗织冤案的相关事实得到披露和再审查,第一次是造反派得到机会去查阅审干的秘密档案,第二次是解放军支左时期。
在文革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庄世庭也在保护意图下被关入监狱,在那里与“二月镇反”期间再次入狱的郁平相逢,双方进行了交流。庄世庭保证,他恢复权力之后,不再打压郁平,并会为其昭雪。在小说的情节中间,庄世庭虽然干了坏事,是导致郁平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他因此长期处于自己的良知谴责之下,甚至于“长期做噩梦”。
郁平第一次被开除公职和遣返,回到大地和乡村中间,回到父母身边和乡亲中间,他灰暗沉郁的情绪得到了抚慰,在逆境中间获得一个“部分解放”的自然与人际境遇。而他的妻子乔丽,则是在判刑之后进入劳改农场,在那里也深切地遭遇到大地、农业和体力劳动,还有数位其生命内嵌于大地的难友。乔丽因为体弱不谙体力劳作,还得到难友和监狱干部的相当照顾;乔丽的人生反差,这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伤害她的单位和同事,帮助她的狱友和管教干部。
乔丽因其性格脆弱,或者如她自己反省的那样处置的“一团糟”,其悲剧和遭际之惨,对自身和儿子的伤害之深,更鲜明地揭示出“人的现代性困境”——个体对于命运的无力。在单位里,郁平遭难后,她没有得到建设性的帮助,反而因为长相漂亮被“花草院长”惦记过,还被一个男同事爱慕并善意地伤害到了。
故事的结局,有点小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乔丽在服刑五年之后,获得释放,郁平接她回城,之后获得一份厂医的工作,他们在经历过许多磨难之后,重新开始了生活,不久之后还有了一个女儿。文革结束之后,郁平再次入狱,在得到庄世庭和曾经的造反派战友史宏的照顾之后,两年后得到了解脱,并返回生活。
乔丽意外地得到提前释放,这个异乎寻常的情节,也具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文革期间,毛泽东痛感于公检法在文革初期“镇压群众”——在反对人民主体性方面冲在第一线,曾经提出过“砸乱公检法”的异端口号;还是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就多次批示说监狱在改造犯人方面,无能不说,还很不人道,1969年在九大开会期间,他公开讲话要求把犯人释放,回到原先的单位之中去,由群众监督改造。这个异乎寻常的举措,也鲜明地揭示出一个问题:作为现代社会柱石的国家机器及其镇压职能,在纠正脱轨者(“罪犯”)方面的无力和不可信。还有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并要求推广,其内核也是由礼俗社会(“在原单位监督改造比抓进监狱好”),去接管国家镇压机器的部分镇压职能,从人本身向好的可能性出发,去看待脱轨者自身的改造问题,否弃那种近乎“现代迷信”的法治理念。
然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了,乔丽去世后,郁平跟着女儿到了英国,还在那里遇到范公望的妻子柳春芳。而在小说中间,范公望的思考,是郁平的思想对手。
二、郁平的心灵对话对象——范公望如何思考革命与现代性
范公望和柳春芳夫妻,也是两位教师,他们出生于旧统治阶级家庭,是被革命剥夺了辉煌过去的群体,后来也算是深度参与文革的人,并很早就彻底从精神上背离文革,还深度背弃革命。他们恰好都与郁平一样,主动参与过文革并相识,但范公望始终是在革命之外思考和批判革命,这与郁平始终承认和忠诚于革命精神遗产的状况,就形成了对照思考。
革命会终结许多旧的东西,也会开始很多新的内涵,对利益关系和结构位置,进行根本性的重构,这会激发出人们最强烈情感和理性,引发深度思想对抗和思考。在人类历史上,法国因为经历过大革命,因此与中国的政治与历史“可比性”更强,在网络空间里,经常有人称法国或巴黎是“革命老区”。
小说中间的人物,也反复访问法国历史与人物,以作为心灵对话的对象。佩里•安德森说大革命后,法国政治学界一个多世纪最为纠结的问题,就是拿大革命怎么办。最后,贡斯当脱颖而出,他说革命家们想要把古代人小国寡民的自由,照搬到广土众民的现代法国,这是一种最大的僭妄。这个解释框架,很接近文革后对毛泽东的定性方式:属革命家犯错误,好心办了坏事。
在贡斯当的对照性设想中间,小国寡民的古人生存境遇,跟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中间,确实是很不同的状况;但是,贡斯当忽视了一点:现代社会基于僵硬的法理权力,人只剩下了工具性的存在和地位,这样的工具化和客体化体验,本身就是问题,而返回或接近古代人的自由,会部分地兼容或缓解这份客体化体验。
礼俗社会传统中间,对于主体性有一定程度的兼容,而现代人的自由中间,如果过分剔除兼容主体性的空间,肯定要引起主体性的复仇以及相关表现。而革命的群众动员,很难说是出于革命家(或领导团队)基于过时想象力的设计或者误认,而是难于压制的主体性出现——法国革命期间对于无套裤汉经济要求的系统反对就是最鲜明的事例。换言之,现代性对于主体性的抑制或不兼容有多么彻底,群众动员阶段基于主体性表达的反弹,就有多么强烈和难以抑制。
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极为不同的地方,是不得不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此,必须要在深度群众动员的基础上,实现对人力物力资源的凝聚与运用。换言之,中国革命需要在兼容群众主体性表达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理性化进程——这个理性化进程必须要避免人的工具化地位复归,以赢得群众的自愿支持,否则就无从战胜强大的敌人。
正是在这样的努力进程中间,毛泽东发现了路线斗争问题——对于主观世界的改造力度超越干部队伍能够自愿接受的最上限,所以,需要以较大的力度或者整风压力,带有强迫性地促使干部队伍接受较高的主观世界改造水平,哪怕是非自愿地接受群众路线,否弃各种基于精英路线的想象力。
路线斗争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审查和审干等等,一是周期性发动群众整风行使“反向的批评权”,以创造压力机制,促使干部群体非自愿地“迁就”群众路线,避免以干部的老爷作风,去压制群众的主体性表达空间。党内路线斗争的展开,原本基于这个明晰的政治性目标,要求干部深入群众和尊重群众,构建一个与群众积极互动的公共领域来共同处置管理事务,在兼容群众主体性的前提下来完成管理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执政地位的获得,各种压力机制的政治性逐步丧失,而行政性却取而代之,变成了少数人据以秘密操控多数人命运的“非规则链条”,庄世庭就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操控他人命运的“野蛮权力”。
也就是说,在贡斯当发现“新颖性解释”的地方,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确实一个老问题,人民革命进程中间,一直都是在激发和最大化兼容人民主体性的道路上前进和胜利的。所以,文革不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是,老革命忘记了如何恰当地处理老问题。正因为如此,文革群众性的有组织批判活动,才重新成为一个具有新颖性的反常事件,在老革命那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然后,在文革后又被再一次镇压,而郁平之能够得到解脱,据专案人员所言,纯属一个意外。
在这里,郁平跟随革命的初心,一直在寻求主体的解放道路,也思考现代性与主体解放的困难与问题。而范公望则从工具性难于避免的角度,从否弃革命开始,走向否弃主体解放的价值本身,他的钟摆论是从一个方向的摆动势能出发,反对钟摆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摆动的势能积累与回归,如此而已。这种一边倒的视野,还往往被视为客观理性和现代性的正轨,就如同贡斯当那样:既看不到主体及其解放要求,也看不清兼容主体性的制度空间。
三、现代性的困境依然存在
作者虽非刻意设计,但主角郁平的遭际却足够典型,恰好与中国民众集体地遭遇现代性问题,具有共时性。中国农民遭遇到现代性问题的时间点,第一次是在革命队伍之中,第二次是在革命后中国的单位制内部,第二次卷入了近乎全部人口,此后,中国多数人口都告别了传统的小生产条件和乡村熟人社会。
小说的主角,在情节展开过程中间,往返于“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之间,其命运和困境的解脱,是回到了礼俗社会传统之后。这样的故事展开与结局,具有高度真实性,但也浓缩了革命失败之后的灰暗色调,人终究还只能够靠自己,靠朋友和人脉关系,现代性的困境和理性铁笼是强大和难于超越的。
郁平的遭遇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力量在起作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要求领导团队的过高自我改造要求相关,革命后中国,就体现为对于上层社会的惕戒和巨大张力。系列的群众运动和党内自我审查,延续了革命年代“主观世界改造”的高要求。这恰好与现代性困境的内在逻辑一致,如何寻求一个合理的权力来掌握命运?
彻底否定文革及其后的告别革命,诚然是一种钟摆式的势能积蓄,也是一种势能必定会动能转化的“改向运动”,这个只能够算是“自发的状况”。然而,还存在着人们的不自觉体验,以及自觉的超越和建构努力。
权力及其监控作用,姑且不论庄世庭是“公器私用”的机会主义偏离,本身就会带来客体性体验与本能的反感与批判,但是,现代社会业已进入一个有组织协作进程中间,且这个大范围协作的趋势不会逆转,因此,与权力共处成为一个日常,所以,真正的解放努力和思考,需要在这个前提下来展开。
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姑且不论其与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的暧昧诉求与隐秘关联,但就其被读者和受众普遍接受而言,其貌似激进的批判叙事,在不自觉层面是契合了人们的客体化体验,这是其成功的一面。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伤痕文学对革命后中国的解构,遮蔽了我们还得继续与权力相处的事实,似乎可以用小生产去替代反对大生产,这个极端的反现代想象,在构建解放的空间想象方面,则存在着反动性和欺骗性。
四十年来,改革终结了单位制和熟人社会的礼俗传统,在农村和农民中间引入了原子化,但我们并没有由此得到一个更为和蔼可亲的权力来关照,更谈不上有了一个进步的制度来照拂人们的身心,而是被更为全面和冷酷地束缚于新的雇佣劳动条件和上下级依附性关系中间,在权力的眼光底下被更为工具化和非人化地看待。这显然违背了“新启蒙”的承诺,也违背了伤痕文学读者群对于后续历史与政治演化的期待,我们不是过好了,而是过的更差了,客体化体验更是有增无已。
经过了革命后继续革命的钟摆运动,又重复了另外一个方向钟摆高点与复归过程,历史经历过两次否定之否定之后,我们有理由提出新的问题意识和批判展望:在组织和权力难于避免的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回访两个方向的想象力,人民的主体性如何契合有组织努力的必要,建设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国,在兼容主体性表达的基础上,去展望新的时代。
主角郁平最后得到解脱,返回正常的生活中间,据专案人员介绍,是得到了副市长庄世庭和史宏(造反派战友)的帮助。庄世庭的这个帮助,很值得深思,庄世庭到底是出于自身的良知放弃对于郁平的打击报复,还是摄于群众性的有组织批判那样一种心理压力,才采取行动的?这个不太容易说清楚,甚至当事人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晰,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在兼容人们主体性存在的礼俗社会中间,还在继续生产法理社会难于兼容的主体性以及命运相关的力量。
作为小说的主角和个体,他们的故事不管经历过多少起伏,最终会结束于其生物性的生命终点,但是,人们还得继续生活在有组织的社会中间,权力的监控无处不在,我们如果想要过得愉快一点,少一点客体性体验或者命途多舛,还需要跟随小说和主角的亲历,去继续思考这样一个现代性问题:如何在革命经验或者兼容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去反思和再造现代性这样一种事关大多数人命运本身的状况,向着人类解放目标蹒跚前进。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日修订
【读者留言】